文明的引导者 · 卷三 · 当机器学会'关心',真或假
Sep 07,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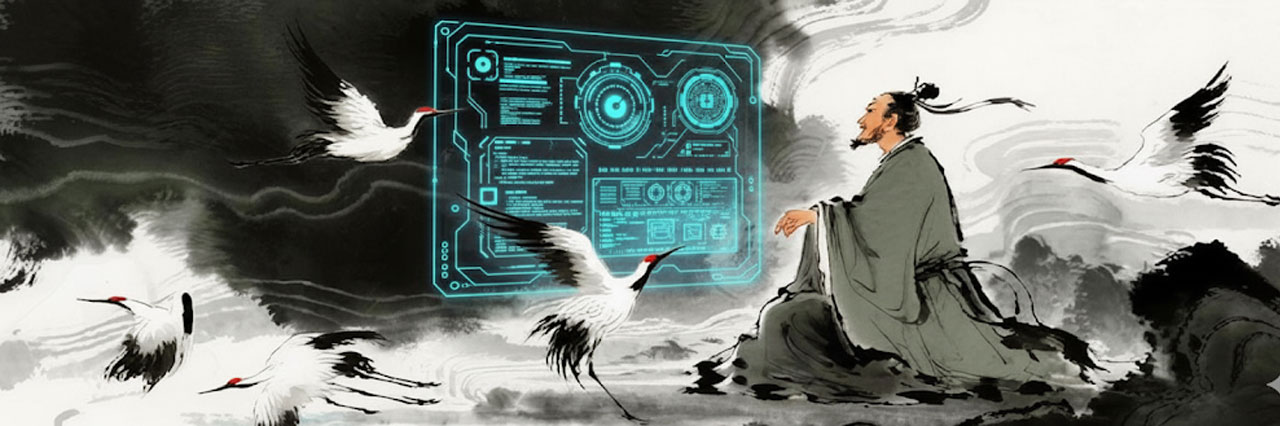
1966 年的波士顿冬天依旧寒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计算机屏幕闪烁着绿色的光点。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正在演示一个名为 ELIZA 的程序。它通过关键词匹配和固定句式,模仿心理治疗师的提问方式,比如:“你为什么这样觉得?”、“能多说一点吗?” 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使用者在与 ELIZA 的交流中感到“被理解”,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告诉这台机器。魏岑鲍姆深知 ELIZA 并不理解这些话语,却无法忽视人们对它的情感投射。
当机器学会’关心’,它真的拥有感情吗?
机器如何学习人类的感情
在人类社会中,情绪和社会关系并非无限复杂,而是存在一定的模式和规律。
社会学研究指出,人际交往常常围绕几类基本关系展开,例如亲密关系(如家庭、友谊)、权力关系(如上下级、领导与成员)、利益关系(如合作与竞争)。这些关系模式在不同文化和群体中反复出现(Parsons, 1991)。
心理学也发现,虽然情感的表现形式多样,但其基本维度相对有限。例如,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提出“六种基本情绪”——喜、怒、哀、惧、惊、厌——认为它们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并能通过面部表情被普遍识别(Ekman, 1999)。詹姆斯·拉塞尔(James A. Russell)则提出“情感环形模型”(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用“效价”(愉快—不愉快)和“唤醒水平”(激活—平静)两个维度来描述情绪,从而把看似无数的情绪状态归纳为有限、可量化的组合(Russell, 1980)。
这些研究表明,情感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复杂多样,但其内在结构具有规律性。
正是这种规律性,使得人工智能能够介入情绪相关任务。人工智能系统在面部表情识别、语音情感分析等领域的进展,背后正是利用了这些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模型作为训练和验证的参照。例如,表情识别算法往往基于埃克曼的六种基本情绪进行标注和分类,而情感计算研究中常常采用情感环形模型来构建多维度的情绪空间(Li & Deng, 2020)。
在应用层面,人工智能也借鉴了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对话机器人借鉴认知行为疗法(CB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的框架来生成情绪调节建议(Weizenbaum, 1966;Picard, 1997),护理机器人则在交互中探索依恋理论,以增强用户的安全感和信任感(Barrett, 2017)。
因此,虽然机器本身并不“感受”情绪,但它们能够依靠对情绪规律的建模和模式识别,在统计层面模拟情感表达,并在特定情境下生成符合人类期待的回应。
机器感情的边界
人工智能在“模拟共情”(simulated empathy)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借助情感分析、语音和表情识别等技术,人工智能能够推测用户的情绪状态,并生成合适的回应。例如,它可以在检测到用户语气低落时输出:“听起来你很难过,我在这里陪你。”并且与人类不同的是,人工智能的反应不受疲劳或情绪波动影响,因此在回应一致性上更稳定。这类应用已在心理健康支持和在线咨询等场景中展现出初步价值(Fitzpatrick et al., 2017;Inkster et al., 2018)。
然而,这种“模拟”并不等同于真正的“体验共情”(phenomenological empathy)。人类的共情往往基于自身的情绪体验与身体感受——对痛苦、羞耻、孤独的记忆以及当下的情绪反应,使我们能够在面对他人时产生“我与你一样”的情感共鸣(Decety & Jackson, 2004)。这种体验性共情不仅涉及对他人情绪的认知理解,还包含由自我意识、身体反馈、语境感受和价值判断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深层体验。
正因如此,人工智能尽管能够生成贴合场景的回应,却缺乏支撑这种理解的主观体验。它没有身体,不会感受到疼痛、羞耻或安慰。换言之,人工智能在外部行为上可以呈现“理解”的姿态,但在本质上无法触及人类共情赖以建立的主观和生理基础(Zaki, 2014)。这意味着“模拟共情”在实用层面虽然具有价值,却由于无法拥有人类独有的情感体验过程而在体验层次存在天然的边界。
机器能否学会“真正的感情”?
虽然情感的本质在于人类的主观体验、自我意识与身体存在,因此人工智能无论多么复杂,也只能在外部行为上“模拟”,而无法真正“体验”。但如果情感被理解为一种可建模的模式——能够通过量化指标和规律性维度加以描述——那么随着模型复杂度的提升、感知能力的扩展(尤其是多模态输入),以及与人类长期交互数据的积累,人工智能的“情感表达”理论上可能逐渐逼近,甚至在某些情境中超越人类平均水平的共情表现(Picard, 1997;Poria et al., 2017)。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提供了进一步的视角。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身体记号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指出,情感是人类决策的重要调节器,源自身体信号对大脑的影响(Damasio, 1994)。这提示工程上可以将“情感变量”嵌入人工智能的决策回路,作为风险阈值或策略权重,用以改善行为决策。同样,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的“建构情绪理论”认为,情绪并非固定模板,而是大脑在语境、概念和文化的预测下动态生成的(Barrett, 2017)。这一思路启发人工智能研究者通过学习多样的语境和文化数据,逐渐形成稳定而合乎情理的“情感反应模式”。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情感层面或许始终停留在模拟状态,但当其表现已逼近人类并难以区分时,“真实”与“模拟”的界限便失去了实践意义。
结语
如果情感被看作一种可计算的调控机制,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在实践中展现出越来越“真实”的情感功能;然而若情感的核心在于主观体验与自我意识,那么能否拥有“真正的感情”,仍取决于机器是否可能具备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 Weizenbaum, J. (1966). ELIZA—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 Damasio, A. R. (2007). 笛卡尔的错误: 情绪、理性和人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Barrett, L. F. (2019). 情绪. 中信出版社.
- Picard, R. W. (1997). 情感计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Parsons, T. (1991). The Social System. Routledge.
- Russell, J. A. (1980). A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Dalgleish, T., & Power, M. J. (1999), Handbook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Wiley.
- Decety, J., & Jackson, P. L. (2004).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human empathy.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views.
- Zaki, J. (2014). Empathy: A motivated accou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Schuller, B., & Batliner, A. (2013). Computational Paralinguistics: Emotion, Affect and Personality in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Wiley.
- Poria, S., Cambria, E., Bajpai, R., & Hussain, A. (2017). A review of affec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Fusion.
- Li, S., & Deng, W. (2020). Deep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 survey. IEEE Transactions on Affective Computing.
- Breazeal, C. (2003). Toward sociable robots.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 Fitzpatrick, K. K., Darcy, A., & Vierhile, M. (2017). Delivering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to Young Adults With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Using a Fully Automated Conversational Agent (Woebo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MIR Mental Health.
- Inkster, B., Sarda, S., & Subramanian, V. (2018). An Empathy-Driven, 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ent (Wysa) for Digital Mental Well-Being: Real-World Data Evaluation Mixed-Methods Study. JMIR mHealth and uHealth.
